刑事案件中虚拟币价值认定困境
断卡行动开始以来,受严厉打击与严格管制影响,使用传统支付平台转移网络犯罪资金的案件呈下降态势,而交易所在海外的虚拟币,因其快捷、匿名、追踪困难等特征逐渐被该类犯罪分子青睐币赢虚拟。相较于传统支付平台,虚拟币可以为更多种类上游犯罪提供支付结算,犯罪行为隐蔽更强,取证难度较高。侦查困难延续到了审判阶段,在相关案件中,对涉案虚拟币的准确价值认定成为准确定罪、精准量刑的关键。
目前我国对虚拟币的态度是模糊的,出于国家金融稳定角度考虑,国家切断了所有虚拟币与法定货币的流通,明确虚拟币“非货币”属性,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从事虚拟币发行融资活动,但对持有虚拟币行为未有界定,其价值认定也无法可依币赢虚拟。一种认定虚拟币价值的方法类似于“市场法”,如在江西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人民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虚拟货币追踪报告显示,被告人李某军陆续将384个以太币转入收款钱包时的价值约为43万元人民币,即为“市价”,最终认定盗窃数额即为43万元。另一种方法是以销赃、买入等交易价格认定其价值,上海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某窃取的虚拟币(泰达币)189万余枚,共计价值人民币1200万余元,其价值认定依据是虚拟币交易价格信息平台发布的历史数据,但被告人罗某在取得上述泰达币后将其兑换成以太坊(ETH)及比特币(BTC),并将部分以太坊向他人出售,共计获利90余万元,最终法院以实际获利90余万元认定其盗窃数额,与公诉机关指控数额差距极大。
以上两种方法均有其局限性,第一种类比“市场法”与虚拟币相关管制文件存在冲突,不可否认的是,在境外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中有符合当地法律规定并实际进行的不间断频繁交易,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中明确指出,任何所谓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为代币或者虚拟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因此“市场法”的根据,即被认可的虚拟货币价格公示机制在我国是不存在的币赢虚拟。第二种方法虽无法律风险,但适用面过于狭窄,司法实践中涉虚拟币犯罪被查处时往往仍处中间环节,未兑换为法币或仍以虚拟币流通,在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中较为常见,存在销赃环节且销赃数额被明确掌握的案件数量并不多。解决上述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应将虚拟币纳入刑法意义上财物的范畴,此为虚拟币价值认定之前提币赢虚拟。早期刑法制定时多考虑有体物品而未将无体物纳入,后伴随着时代发展,无体物逐渐纳入刑法评价范畴。目前虚拟币虽然出现的时间较短,其也多与黑灰产业相近,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虚拟币为代表的虚拟财产已经事实成为现实财产的一种,具有可管理性、转移可能性和价值性,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其所凝结的劳动或资产投入是客观的,具有财物的一般特征,将虚拟币解释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也符合用语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的发展趋势。
其次,应当探索建立虚拟币价值平衡认定机制和幅度量刑机制,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对涉案虚拟币价值进行采样确认,以确定其整体价值,在具备法定“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其他犯罪成立的必须条件前提下,按量刑情节而不按照数额量刑,在判断情节是否严重时,应综合考虑行为的次数、持续的时间、非法获取虚拟币的种类与数量等,降低前述认定价值的参考比重,以降低因虚拟币涨跌不均衡而带来的量刑不当币赢虚拟。
最后,应探索建立虚拟币司法处置机制,明确涉案虚拟货币的司法处置原则,建立专门托管平台,参考一段时间内虚拟币交易价格,避免因案件期限等原因不得已低价处置,最大限度保证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币赢虚拟。同时要求第三方机构在处置相关虚拟币时提供全流程跟踪报告,确保处置手段、交易区域、兑现方式合法合规,避免因司法机关集中委托处置虚拟币而催生灰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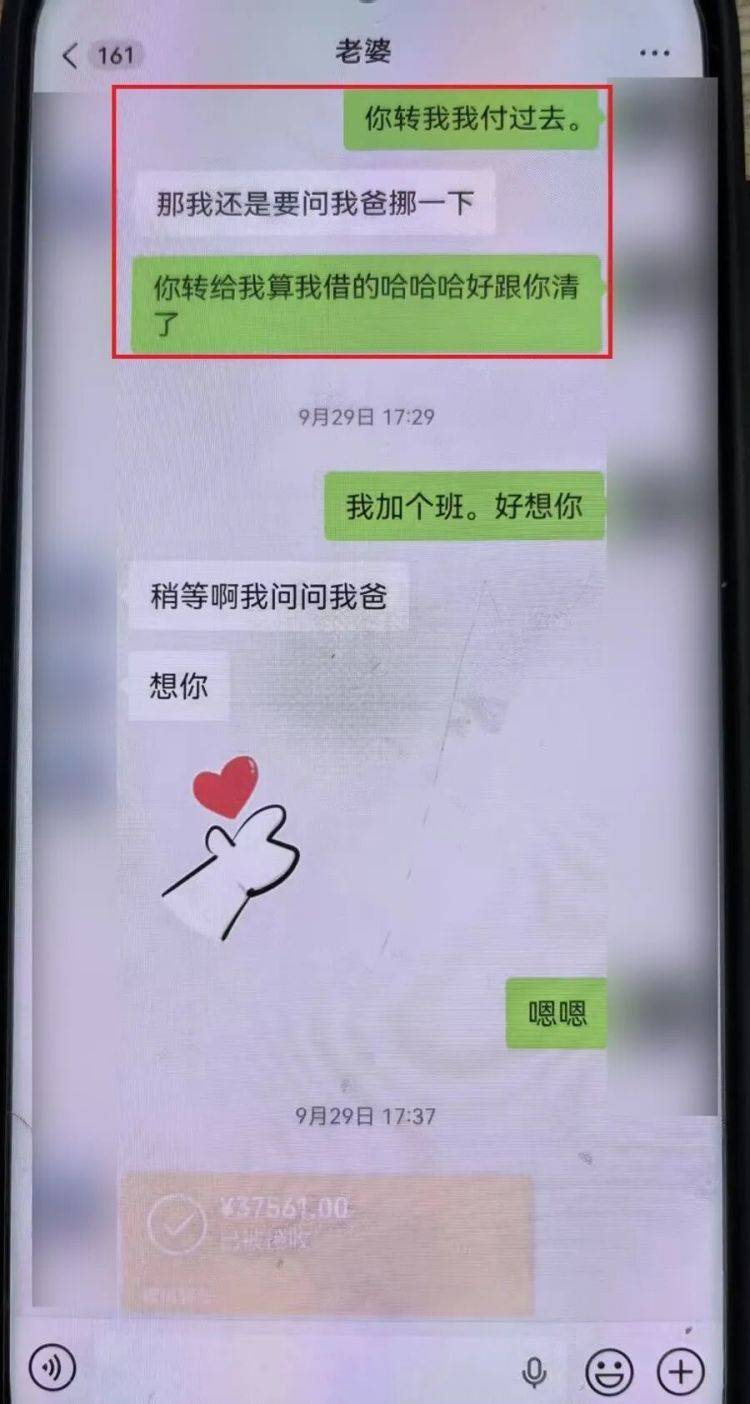
评论